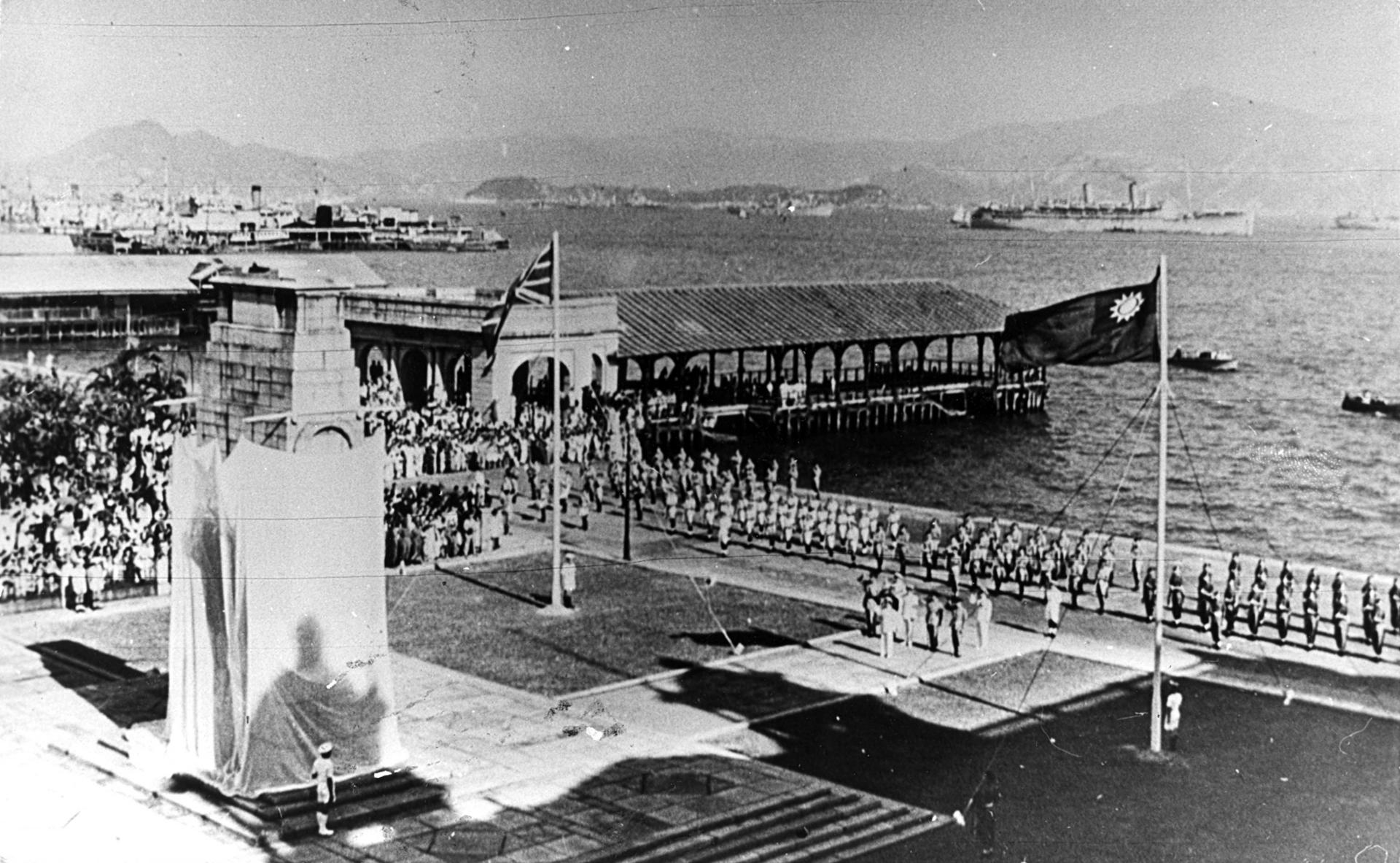偶爾無聊,都會打開放置錢幣的'寶箱',欣賞那一張張猶如相片般記錄了舊日香港的紙幣,這一次就是五張紫色的五十元。紫色五十元的發行年份為1985至2002年,十八年的時間,角式乃輔助十和二十元之用,發行量最少,要在當年的市面遇上一張亦非易事,加上小弟年紀尚幼,無賺錢能力,能得到一張五十元還真不容易,所以小弟在用掉之前都會多看幾眼。
諸君可以從這張五十元的正面全相,看得出匯豐1985年系列的紙幣,依然帶有該行七十年代一百到一千元的身影,但更為先進和美觀。
 |
| 在匯豐的初代細張紙幣之中,二十,一百和一千出現過顏色不同的小改款,十,五十和五百則沒有。 |
小時候的一個傍晚,父親吩咐小弟跑腿到街市的雜貨鋪買豉油,給的就是一張這樣的五十元,而且是簇新的。離開家門在大堂等待電梯的時候,小弟一直把視線集中在那張紙幣上,除了翻來轉去看看紙幣上的字句與圖案,又在燈光下細看防偽的水印和金屬線
,還放在鼻前'嗦'呢。這就是匯豐的紫色五十元為小弟帶來的童年回憶吧。
若說正面保留了匯豐七十年代的鈔票格局,那麼背面就有更多耳目一新的變化,連落成不久的第四代總部大廈也能夠適時登場,更覺時尚摩登,而右面那圓框內的構圖同時為紙幣添上本地的味道,香港的特色也就在隨此流傳。
 |
| 小弟兒時因為這些紙幣的構圖,總以為匯豐總行大樓直接面著一座青翠的高山(太平山),然而太平山與此大廈之間還有一些建築物存在,與小弟的想像極為不同。 |
五十元背右的龍舟競渡圖與同期其他面值紙幣的繪圖份屬不同類型:就是一千元的立法局、五百元的港督府、一百元的虎豹別墅和二十元的尖沙咀鐘樓都是對地上建築物或風景的描繪,只有十元的帆船及貨船圖和五十元的龍舟競渡是全然屬於水上,當中又以五十元像人物的動態描繪多於對景色的描畫。事實上匯豐也沒有明言不同面值紙幣的圖案之間有什麼關聯,這就像謎語或拼圖般值得玩味了。另外一個分類方法,就是將十元和二十元歸類為港口,五十和一百為傳統,五百和一千為權力或建築。
 |
| 左上的龍舟的鼓手坐在中間位置,看來這兩條龍舟都屬較大型者。 |
將要接管香港的支國不願看見太多英國殖民地的色彩,於是匯豐在1993年發行新的,即是第二代'細張'鈔票,以銅獅的圖案取代帶有皇冠的銀行紋章。那是一張2002年匯豐五十元的正面,左方有精神威猛的銅獅施迪Stitt,中間的港島海旁景色即使作為背景亦無礙人們一窺九十年代香港的景氣,將兩者合起來看,就像施迪凝望著維港,意味匯豐與香港的繁榮密不可分。右方的水印為張嘴的史提芬Stephen,與施迪遙遙對望,符合這對銅獅與匯豐的形像之餘也猶如守衛香港一樣。由小至大排列的號碼也為紙幣多添幾分摩登的時代動感。
 |
| 匯豐自1993年款的紙幣起印上'憑票即付'及'承董事會命'等中文字眼,使香港人明白那些例必在港幣上出現的英文語句的意思之餘,也多了幾分本地的味道。 |
究竟1993年款的匯豐紙幣有多少隻銅獅呢?答案是六隻。原來印在票背的匯豐總行大廈的底部就隱藏了一對銅獅,只以小點的形態出現,不用放大鏡細看的話便很容易忽略過去,所以很多人也就發現不到。
首先在發鈔上標示版權的是匯豐銀行。事緣九十年代中期,市面上出現了以舊款匯豐紙幣為藍本的玩具紙鈔,比如說以明星或卡通人物的圖片取代銀行的紋章等等,匯豐便以損害形像和偽鈔嫌疑等理由取締這些玩具,又從1995年版的紙幣開始印上版權標示。渣打和中銀的鈔票要到2003年更換設計時才有同類的東西。
將兩代匯豐五十元的背面的龍舟競渡圖相比,1993年款富有當年時尚的電腦構圖感覺,以線條為構圖主調,感覺硬朗;1985年款則傳統味濃,光暗分明而觀感柔和。當港幣在2003年改版後人們以為扒龍舟不會再成為鈔票的構圖,匯豐卻在2010年系列的千元'金牛'的背面印上龍舟競渡的圖案,又配上'端午'為題。如以現在的說話表達,2010年款一千元就如高清電視的播放畫面,不論光暗與線條亦能兼顧,活靈活現,1993年款五十元就如上所述,像九十年代的電腦製作圖,而1985年款五十元就更像那個年代的彩色電視,螢幕顯示的色彩多於線條。畢竟科技在二十多年時間也進步不少。
 |
| 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以往不能細膩表現的部份在今天已不是難題。此圖已清楚顯示二十五年的進步空間有多大。 |
匯豐的紙幣在千禧年代的香港市面還是佔了絕大多數,要自然地遇上(指購物時經找贖得到)一張該行的五十元已經有一定難度,若然要得到渣打或中銀的當然難上加難。與匯豐相比,渣打的初代細張紙幣更明顯地延續了自家末代中張的特式,很多相同的元素在日後的渣打發鈔上繼續出現。即使如此,這隻踩波(戲球)的獅子和牠鎮守的五十元還是經歷了較明顯的改變,就是由藍色變成紫色,不過就顯得更有神氣,人見人愛了。當然中張不屬我們的討論範圍,所以我們現在就看看正面的全相。
 |
| 與匯豐和中銀不同的是,渣打在九十年代仍然有單字母字軌的鈔票出現,後來也沒有了。 |
然後是背面。
 |
| 即使渣打的第三代總部大廈已於1987年拆卸,但其形像依然留在渣打紙幣的背面至1992年。 |
但坦白說,小弟對這款帶紋章的渣打五十元沒有甚麼記憶,反而對十元和廿元的印像還有一點,這可能是兒時能接觸金錢就只有農曆新年和平日跑腿的時間,使小弟一有機會便緊盯這些接觸不多但又非常吸引的錢幣。
 |
| 記得中學時讀報,得知有人以渣打的五十元參加美術比賽,當中位於右方的獅子是立體的小雕像,而那份作品好像又奪得獎項。 |
升讀中學以後,接觸金錢的機會增多,這時的渣打紙鈔早以略作改動,正面的就有:
 |
| 舊款的渣打紙幣被香港的收藏家稱為'長棍',源於正面最左方那刻有幾何條紋的長條,由底部一直伸延至上角處那面額數字的背後。自1993年系列開始,那條長條不再伸延至數字的背後,故又有'短棍'之稱。 |
 |
| Hong Kong的擺位也出現變化,這圖亦正好表現了新舊鈔票的顏色減淡現像。 |
背面的變化較正面明顯。不得不說,即使渣打鈔票的背面很是簡單,但其可塑性高,只要將紋章換成紫荊花朵便可,不像匯豐的紙幣需要重新設計。
 |
| 甚麼是'簡單就是美'呢?這一代渣打紙幣的背面就是一個例子。 |
 |
| 對小弟來說,當然是渣打的皇家紋章好看過紫荊花朵很多啦。頂上的方格也物盡其用成為'香港渣打銀行'六字。 |
 |
| 兩代渣打總行大樓。雖然線條幼細,然而光暗位置的描繪與四圍的色澤又使舊總行大樓看來被詭異的氣氛所包圍;新大樓以粗擴的線條繪畫,現代而簡約。同時'伍拾圓'和'50'等字的色澤亦變深。 |
小弟對支資機構一向都沒有好感,但不得不承認,中銀紙幣的設計其實不差,尤其是背面佔票幅三分二的風景圖,生動地展現了香港獨特的一面之餘,也開創了日後港鈔設計的先河。在1994年款中銀五十元的背面就是灣仔的海底隧道入口,往九龍方向還能見到一段車龍哩。猶記得九十年代中期的早上,某電視台的早晨節目都會報導香港不同交通要點的狀況,海底隧道的出入口必然在內--而且都是擠塞的,當年還處於童年的小弟只覺事不關己,還趁著父母外出工作時偷玩遊戲機和偷看電視哩。直至近年駕車,經常駛經紅隧和東區走廊(見背面風景圖的右上角),飽受塞車之苦的時候,方才發現童年時那份簡單的心是多麼的天真和奢侈。
 |
| 從這個角度應該遠眺到啟德機場的跑道,就在'中國銀行'四字的正下方,只是沒有刻劃出來,反而這個系列的一千元背面的中區風景圖就描繪了一點點啟德跑道的輪廓。啟德機場其實也是八九十年代香港的標誌之一。 |
 |
| 中銀高層向來在發鈔上以中文簽署,而且字體細小,不如匯豐和渣打大班的英文簽名般飛逸順暢。 |
中銀在香港的首次發鈔在1994,屬第二代的'細張'港鈔。 若要找出1994款中銀紙幣在正面的特色,那就應該把目光集中在正中的部份:先是下部的花卉,不同面值有不同品種,在五十元的是菊花;然後是由'見票即付'一句到菊花圖案之間的背景構圖,也是不同面值有不同色彩;最後是頂部'中國銀行'四字後面的紫荊花背景:二十,五十和一百元的是一款,五百和一千元則是另外一款。
 |
| 根據觀察,二十至一百元等低面值紙幣的紫荊花有明確且分開的花瓣和花蕊,五百和千元大鈔的紫荊花就只有輪廓,花瓣和花蕊連在一起。 |
說到正面處,自然要說說那個簽名的香港分行總經理--劉金寶了。據云此人曾經促成中銀在香港的重組和上市,然後又因貪污等罪名失勢,真不知道是他罪行嚴重還是支共過橋抽板的一貫做法。總之由2003年系列開始,中銀鈔票正背都印上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的名稱,簡稱為中銀香港。
隨著港共政權在2002年發行'花蟹'十元紙幣,加上香港紙幣需要改版,五十元的色調就在2003年系列起改為綠色,渣打的踩波獅子也就此與羅馬兵水印雙雙退下。然而綠色的五十元又與匯豐及渣打的'青蟹'十元接近,故有時評港共'阿茂整餅'--無嗰樣整嗰樣,後來香港人也就習慣了。至於五十元,則一直是輔助的角式,數量不如十元和二十元般普及,要到2010年改版後才有更多機會在市面找到。
小弟生性懶散,很多文章不是拖泥帶水很久才完成,就是業已'爛尾'不知能否寫完的狀態,畢竟吃飯緊要,遊戲性質的事只能放到一旁。直至2018年系列,即是第五代的'細張'港鈔發佈之後,小弟方發現最後的紫色五十元(2002年版)至今已經有十五六年了,不得不感嘆時光的飛逝。於是小弟就只能盡快趕工,希望在新鈔流通前跟諸君分享一下這些不太常見的五十元吧。
參見: